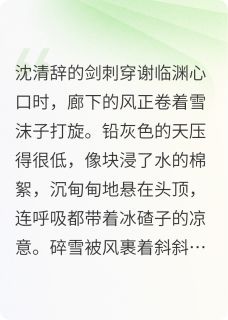
科幻小说《剑落时》是爱吃剪刀面的沈清岚的代表作之一。主角沈清辞谢临渊归尘剑身临其境地展示了未来世界的奇妙景象。故事充满了科技和想象力,引人入胜。这本书不仅带给读者无限遐想,也让人思考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影响。眼里没有惊讶,只有温和笑意:“小姑娘,别怕,以后我护着你。”那时她刚从乱葬岗逃出,……
沈清辞的剑刺穿谢临渊心口时,廊下的风正卷着雪沫子打旋。铅灰色的天压得很低,
像块浸了水的棉絮,沉甸甸地悬在头顶,连呼吸都带着冰碴子的凉意。
碎雪被风裹着斜斜打在雕花廊柱上,那些刻了半世的缠枝莲纹本是暖色调,
此刻却被雪光映得发白,像蒙了层薄霜。
飞檐翘角积起的薄白衬得檐下宫灯愈发红得刺目——那红太烈,
像极了十二岁那年沈家大宅漫开的血色,漫过青石板,漫过朱漆门,
漫过她蜷缩的假山石缝隙,连空气里都飘着化不开的腥甜。她握剑的手稳得反常,
指节因用力泛白,死死扣着玄色剑鞘上绣的寒梅。丝线是用陈年墨汁染的,
在雪光里泛着沉乌,倒让那几朵半开的梅苞有了铮铮骨相。那寒梅是师父亲手教她绣的,
三年前她刚到听雪阁时,性子躁得像团火,练剑稍不顺心就摔剑,是他把绷子架在窗台上,
执起她的手教穿针引线。“你看这梅枝,”他指尖蹭过她手背,常年练剑的薄茧带着暖意,
“看着软,骨子里是韧的。雪越大,开得越烈,这才是活下去的样子。”三年来,
这柄“归尘”剑被他摩挲得光滑温润,剑鞘上的寒梅在掌心反复打磨下,竟有了玉的莹润。
剑穗上的流苏是她去年生辰编的,青蓝丝线绞着银线,她当时笨手笨脚,拆了又编编了又拆,
最后是他坐在灯下替她理线团。“这样绕个结,”他手指穿过她指缝,
带着她系好最后一个结,烛火在他睫毛上投下浅影,“清辞编的,便是最好的。
”如今那青蓝流苏沾着他的血,红得发黑,像极了被墨汁浸过的血痂,在风雪里轻轻晃,
晃得人眼晕。“为何?”谢临渊的声音很轻,像风中将断的丝线。他垂眸看胸前的剑,
银丝般的雪落在苍白鬓角,混着未干的墨痕——方才他还在书房为她批改剑谱,
笔尖的浓墨还没来得及干透。案上的端砚里,墨锭斜斜搁着,旁边压着她写废的剑谱,
“回风式”三个字旁,他特意画了小小的箭头,标注“腕力稍收”,朱笔在雪光里泛着暖,
像他总为她温着的茶。血珠顺着剑刃淌下,在月白衣襟洇开,像朵骤然绽放的红梅,
妖冶得让人眼疼。沈清辞望着那抹红,忽然想起去年重阳,她偷喝了他藏的桂花酒,
醉得趴在石桌。他抱她回房时,她迷糊着抓他衣袖不放,闻到松烟墨香混着雪后松林的清冽。
那晚梦很长,母亲牵着她走在沈家后花园梅树下,花瓣落发间,暖得像春阳,
母亲鬓角的珍珠钗在日光里闪,和师父书房里那支玉簪很像。“为何?”谢临渊又问,
声音带了不易察觉的颤抖。他抬眼望她,那双总是含着温和笑意的眸子蒙着雾,
雾里有细碎的光在闪,像将熄的星子。沈清辞却在那雾里,跌回十二岁的雪夜。
那晚的雪更急,鹅毛似的砸下来,把青石板铺得软软的,踩上去悄无声息。她缩在假山石后,
怀里揣着母亲塞的半块玉佩,棱角硌得心口生疼。母亲推她进去时,发间金簪掉在雪地里,
“叮”的轻响竟比父亲的惨叫还刺耳。她看见玄衣人影站在父亲面前,长剑挑着父亲衣襟,
父亲挣扎着要扑过来,却被反手一剑刺穿咽喉。血喷在玄色衣袍上,像此刻归尘剑上的红,
只是那晚的血更烫,隔着石缝溅在她手背上,三年来每次想起,都要打个寒噤。“师父可知,
沈氏满门七十二口埋在乱葬岗时,也是这样的雪天?”沈清辞的声音冷得像冰,可每说一字,
心口就被钝刀割一下。
那些刻意压下的温暖正疯长着刺破冰层——去年她练“惊鸿式”摔在青石地,
膝盖磕出好大一块血。他蹲在廊下替她上药,药粉撒在伤口疼得她抽气,
他便哼起不知名的调子,软软的像江南吴侬软语。她盯着他发间雪粒,忽然就不疼了,
只记得他指腹擦过她眉骨时,带着棉布般的温软。她练剑扭伤脚踝,
他背着她走过落满银杏叶的小径,步子稳得像踏在云端。银杏叶在脚下沙沙响,
他说:“清辞你看,这叶子黄得像金箔,捡回去压书签好不好?”她趴在他背上,
闻着衣领间墨香混着阳光皂角味,忽然就不想下来了,偷偷数他发间的银丝,
数着数着就笑出了声。甚至有次她赌气说想吃城南桂花糕,第二日清晨,他衣襟沾着霜,
手里捧着油纸包的热糕。油纸被热气熏得软塌塌,他解绳结时,
桂花甜香漫出来:“刚出炉的,快吃,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她咬着糕,
看见他睫毛上的霜粒在晨光里闪,心里忽然就软了,偷偷把最大的那块塞回他手里,
假装没看见他眼底的笑意。谢临渊忽然笑了,咳着血笑的,笑意漫过嘴角,
眼底却凝着化不开的苦。“原来……你都记起来了。”他抬手,指腹带着练剑的薄茧,
似要碰她冻红的脸颊,却在半空猛地一颤,重重垂落。他袖口银线绣的流云,
是她前几日帮他缝补的,当时她抱怨云纹复杂,针脚歪歪扭扭,他却说:“清辞缝的,
便是最好的。”他没说完。身子晃了晃,像被狂风折断的翠竹,重重倒在雪地里,
溅起碎玉似的雪粒。乌木发簪滚落在地,散开的长发铺在雪上,黑得像深潭,
衬得那张脸愈发苍白如纸。发间还别着朵干白梅,是上个月她折来给他簪的,
说“师父戴花最好看”,他当时笑着没摘,如今花瓣被雪打湿,软塌塌贴在鬓角,
像她哭皱的帕子。沈清辞站在原地,看师父逐渐失焦的眼,握剑的手终于抖了。
归尘剑的剑柄被掌心焐得发烫,剑上血迹开始凝固,成了暗沉的红。她想起三年前初见他,
他也是一身月白长衫,站在沈家旧宅废墟前,雪落肩头像覆霜。他转身看见她,
眼里没有惊讶,只有温和笑意:“小姑娘,别怕,以后我护着你。”那时她刚从乱葬岗逃出,
浑身是伤,形容枯槁像受惊的小兽。是他把她带回听雪阁,为她疗伤,教她剑法,
给她取名清辞。“清者,澄澈也;辞者,言词也。”他执她的手在宣纸上写字,笔锋舒展,
“愿你心明如镜,言出有信。”她当时嫌这名字不如“明玥”亮堂,却没敢说,
只偷偷在沙盘里写了无数遍“清辞”,看那两个字在月光里泛着浅痕。三年来,
他从未对她发脾气。她练剑心不在焉,把剑招练得乱七八糟,他只笑着摇头重新演示。
“你看这‘流风回雪’,”他提剑在雪地里起舞,衣袂翻飞如白鹤振翅,“要跟着风走,
不是跟剑较劲。”雪花落发间肩头,他浑不在意,眼里只有她错愕的脸,像藏着整片星空。
她闯了祸,把镇北王的小儿子打成熊猫眼,是他连夜登门赔罪,回来时额角带伤,
却对她说:“清辞,下次下手轻点,别脏了你的手。”她当时只觉他窝囊,
如今才想起镇北王爪牙遍布京城,那句轻描淡写里藏着多少凶险,他宽袖下的手臂,
怕是也挨了不少打。沈清辞视线模糊,眼泪砸在剑上,叮当作响像敲碎玉。她想起昨夜,
她练剑到深夜,他端来亲手炖的姜母鸭,汤里放了她爱吃的红枣枸杞。他坐在对面看她喝完,
眼里温柔几乎要溢出来。“清辞,”他忽然开口,带点郑重,“过几日是你生辰,
想要什么礼物?”她正啃鸭腿,含混不清地说:“我要师父陪我去放花灯。”他听了,
眼角细纹都深了些:“好,都听你的。”那时她没看见,他转身时,悄悄用指尖擦了擦眼角,
像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。原来那些温柔都是裹着毒药的糖。沈清辞这样告诉自己,
心脏却传来尖锐的疼,疼得喘不过气。她看倒在雪地里的谢临渊,胸口微弱起伏越来越缓,
血还在渗,染红身下白雪,像她去年画坏的《寒梅图》,墨没调好,红得发暗,
当时她还闹脾气把画撕了,是他一片片捡起来,说“我们清辞画的,碎了也是好的”。
雪越下越大,几乎要埋住谢临渊的衣襟。沈清辞弯腰想收他尸身,指尖触到他袖中硬物。
是块玉佩,温润的羊脂白玉,
雕着沈家云纹图腾——正是母亲当年塞给她、被她慌乱中遗失的半块。她手抖得几乎握不住。
玉佩边角被摩挲得光滑,显然常年贴身戴着。背面刻着极小的“护”字,笔画深透,
像刻了无数遍,边缘都磨得发亮。沈清辞忽然想起,三年来他总在她练剑时摩挲袖口,
那时以为是习惯,如今才明白,他是握着这半块玉佩,像握着一个滚烫的承诺,
握得掌心都出了汗。玉佩下压着半张泛黄的海捕文书,
字迹凌厉如刀:“谢临渊私藏逆党余孽沈氏孤女,查实当诛,同党者斩。”落款是镇北王,
朱红印泥已发黑,却依旧透着森然杀气,像那年闯进沈家的刀光。风卷着纸飞起来,
贴在她冻僵的脸上。沈清辞忽然想起师父没说完的话,
想起他书房那柄从不示人的旧剑——上个月她偷偷摸过,剑穗系着镇北王贴身的白虎令牌。
她还想起每次仇家寻来,总有神秘人提前报信;想起她随口说想查旧案,
第二日书房就多了镇北王的密档。密档里记着镇北王如何构陷沈家通敌叛国,如何伪造书信,
如何买通狱卒。她当时只当是师父偶然得的,如今才懂,那是他费尽心机搜集的,
每一页都浸着他的血和汗,有次她见他手腕缠着绷带,他只说是练剑伤的,现在想来,
怕是为了抢这份密档,跟镇北王的人动了手。
“那剑……是用来护你的啊……”她仿佛听见师父没说完的话在风雪里回响。
沈清辞猛地跪倒在雪地里,怀里紧攥着玉佩和文书,哭得撕心裂肺。雪花落发间肩头,
很快积起薄白,她却不觉冷。手指抚过他苍白脸颊,触到嘴角未干的血迹,已开始变冷变干,
像十二岁那年在乱葬岗摸到的冰冷石碑,碑上没有名字,只有风吹过的呜咽。
“师父……”她哽咽着,声音破碎,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为什么不解释?”无人应答,
只有风雪呼啸,像无数冤魂哭泣。沈清辞想起他书房的日记,以前总缠着要看,
他却笑说:“等你再长大些。”他揉她发顶时,眼里笑意温温柔柔,“就给你看。
”她跌跌撞撞爬起来,踉跄着冲进书房。墨香还在弥漫,书桌上摊着她的剑谱,
朱笔圈点新鲜。端砚里墨锭斜搁,旁边压着张纸,是他刚写的字:“清辞剑法学成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