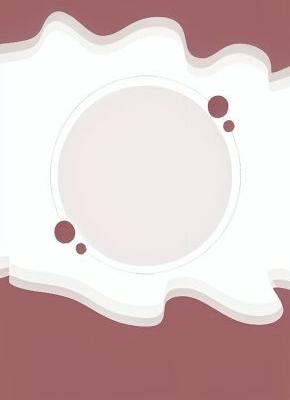
悲剧小说《天鹅肉,好吃么?》以李默林薇薇苏晴为中心,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和社会的残酷现实。作者用户21234238通过犀利的笔触深刻地刻画了主角的内心纠结与挣扎,将读者带入一个情感充沛的世界。这本书给人以思考和反思,震撼人心。他能蹲在别人店门口等到深夜。他老实,送货从不短斤缺两;他嘴笨,但答应的事一定做到。……
1烈日与冷语六月,正午,毒辣的日头悬在头顶,像一只烧红的独眼,无情地炙烤着大地。
空气粘稠得如同融化的沥青,吸进肺里都带着一股灼烧感。H市东郊,
一片巨大的建筑工地如同喧嚣的钢铁丛林,
搅拌机的咆哮、钢筋碰撞的锐响、塔吊运行的嗡鸣,还有工人们粗粝的号子声,
混杂成一股震耳欲聋的声浪,撞击着布满灰尘的围挡。李默弓着腰,
肩上压着一摞至少二十块红砖。汗水像小溪一样从他剃短的头发茬里涌出,
顺着晒成古铜色的脸庞、脖颈蜿蜒而下,浸透了早已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旧工装背心,
在后背洇开大片深色的汗渍。他一步一步挪到正在砌墙的师傅身边,卸下砖块时,
腰部的关节发出不堪重负的轻响。直起身,眼前猛地一黑,金星乱窜,
他赶紧扶住旁边粗糙的水泥袋,才没栽倒。「李默!发什么愣呢!」
工头老张的破锣嗓子炸响,他趿拉着一双沾满泥点的旧皮鞋,叼着半截快燃尽的烟卷走过来,
满是油汗的脸上写着不耐烦,「东边三号楼二层,沙浆!没听见喊吗?等着下崽儿呢?
耽误了进度,扣你工钱!」「来了,张头儿。」李默抹了把脸,手上混合着汗水和粉尘,
抹出一道污痕。他抓起手推车的车把,铁质把手被晒得烫手。
车轮碾过散落的碎石子、钢筋头,吱吱呀呀地驶向搅拌区。尘土被车轮卷起,扑了他一脸。
这就是他的世界。十九岁的夏天,高考失利的闷棍,父亲早逝、母亲多病的现实,
把他从对未来的模糊憧憬里,一巴掌扇进了这片尘土飞扬、汗水与体力兑换微薄薪水的工地。
大学录取通知书?那是别人家的喜讯。建筑艺术?那是书本上和远处玻璃大楼里的幻影。
他的日常,是搬不完的砖,和不完的沙浆,是工棚里永远散不去的汗酸和脚臭,
是每晚躺在硬板床上,浑身酸痛像散了架,听着工友们震天的鼾声和梦话,
盯着天花板上摇晃的昏黄灯泡,计算着今天又挣了八十,
离给母亲买那副好一点的膏药还差多少。傍晚,太阳的余威终于稍稍减退。
李默端着掉了不少瓷的破旧饭盆,蹲在工棚外的水泥台阶上,
囫囵吞着没什么油水的水煮白菜和硬米饭。
盆边放着一个屏幕碎裂、用透明胶带粘着的旧手机,那是他考上高中时母亲咬牙买的二手货,
现在是他与外界那点可怜联系的唯一通道。饭很糙,他吃得很快。洗完饭盆,
他回到拥挤嘈杂的工棚,在通铺自己的位置上坐下,身上汗湿的衣服黏腻地贴着皮肤。
犹豫了很久,他终于还是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旧手机,指尖在碎裂的屏幕上滑动,
最后停在一个头像上——苏晴。那是他灰暗青春里,唯一的一抹亮色,遥远,模糊,
却顽固地存在着。高中不同班,大学更是天壤之别。一次偶然的志愿者活动,
他们被分到一组,发宣传单。她穿着干净的白裙子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,声音轻柔。他笨拙,
话少,搬重物时却很利索。她递给他一瓶水,说:「同学,辛苦了。」后来,
他们加了社交软件好友,聊过几次天,关于学校,关于未来模糊的想象。
她分享过喜欢的音乐,他偷偷听了很多遍;她提到市图书馆偶尔有不错的展览,
他记在了心里。再后来,她去了省城一所不错的大学,朋友圈里的世界越来越光鲜,
与他泥泞的现实彻底割裂。联系渐少,最后只剩下偶尔朋友圈点个赞,
像隔着厚厚的毛玻璃看一场无声的电影。但那个影子还在。手指有些僵硬。
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敲,删掉,又重敲,反复几次,终于按下发送:「苏晴,周末好。
听说市图书馆新开了个建筑艺术展,挺有意思的,不知道你这周末有没有空?」发送成功。
心脏在胸腔里突兀地跳得很快,带着一种混合了渺茫期待和深深自卑的钝痛。
他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铺位上,不敢再看,起身想去外面透口气,却又挪不动脚步,
眼神总忍不住往那小小的机器上瞟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
工棚里充斥着工友们打牌吹牛的喧嚣,烟雾缭绕。李默觉得自己的等待,
在这片浑浊的热闹里,显得格外寂静和可笑。不知过了多久,也许半小时,也许更久。
手机屏幕终于亮了,震动了一下。不是苏晴的回信。是一条语音消息,
来自一个陌生的、但又隐约有点印象的头像——好像是苏晴的一个闺蜜,叫什么薇薇的,
在苏晴朋友圈合照里出现过,很漂亮,也很耀眼的样子。李默的心沉了一下,点开语音,
下意识贴到耳边。下一秒,一个刻意拔高、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讥诮与轻蔑的女声,
尖锐地刺破工棚的嘈杂,也刺穿了他的耳膜:「哟!我当是谁呢!这不是李默吗?」
语音是外放的。旁边几个工友停下了手里的牌,看了过来。那声音继续,语速很快,
字字如刀:「怎么着,在工地搬一天砖挣那七八十块钱,就癞蛤蟆惦记起天鹅肉了?
还敢来约我们晴晴?还建筑艺术展?李默,你看得懂吗你?你分得清哥特式和巴洛克吗?
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吧!一身的水泥灰,隔着一百里地我都能闻到你身上那股穷酸汗臭味儿!
我告诉你,晴晴跟你压根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!少在这儿白日做梦了,赶紧搬你的砖去!
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你也得先问问自己配不配啊!」语音播完了。
工棚里出现了几秒钟诡异的寂静。打牌的、聊天的,都停了。所有的目光,有意无意,
都落在了李默身上。那目光里有同情,有麻木,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看热闹,
甚至有一两声压抑不住的、极低的嗤笑。李默僵在原地。手里那个破旧的手机,
此刻烫得像一块烧红的炭。浑身的血液似乎轰的一声全部冲上了头顶,
脸颊、耳朵烧得刺痛;紧接着,又猛地退潮般褪去,只剩下刺骨的冰凉,
从脚底板一路蔓延到指尖,冻得他微微发抖。
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脸上的肌肉在不受控制地抽搐,耳边是嗡嗡的轰鸣,盖过了一切声音。
那个叫林薇薇的女人,他甚至没见过她几面,她的声音却像淬了毒的冰锥,
精准无比地扎进了他心底最脆弱、最自卑、拼命想隐藏的地方。不仅仅是因为她对「癞蛤蟆」
的嘲讽,更是因为她毫不费力地,用最轻蔑的语气,
把他和苏晴之间那层自欺欺人的窗户纸捅得粉碎,
把他试图踮起脚尖去触碰的那一点点遥不可及的幻想,踩在脚下,碾进泥里。「看什么看!
不用干活了?」工头老张的吼声打破了沉寂。工友们讪讪地转回头,牌局和闲聊重新开始,
但气氛已经变了,一种微妙的、令人难堪的窃窃私语在弥漫。
李默慢慢地、极其缓慢地按熄了手机屏幕。最后一点光消失,映出他眼中一片死寂的黑暗。
他没有再看任何人,沉默地站起身,走出工棚,走进外面沉沉的夜色里。
夏夜的风带着未散的暑气,吹在他汗湿的背上,激起一层冰冷的战栗。
他走到工地边缘堆放的建筑材料后面,背靠着一根冰冷粗糙的水泥管,缓缓蹲下。
手指插入短发,紧紧攥住,指甲抠进头皮。没有眼泪,
只有一种近乎窒息的、冰冷的愤怒和巨大的耻辱,像黑色的潮水,淹没了他。不知蹲了多久,
腿都麻木了。他抬起头,望向城市的方向。那里灯火璀璨,勾勒出高楼大厦梦幻般的轮廓,
与他身后这片黑暗、嘈杂、尘土飞扬的工地,泾渭分明。苏晴的世界。林薇薇的世界。
一个他拼尽全力也挤不进去的世界。「呵……」一声极轻的、带着血腥气的嗤笑,
从他喉咙里逸出。他重新拿出手机,屏幕碎裂的纹路割裂了微弱的光。
他找到林薇薇那条语音,点开,又听了一遍。每一个字,都像鞭子,
抽打在他早已伤痕累累的自尊上。然后,他按下了保存。接着,他点开苏晴的对话框。
那条他斟酌许久的邀约,孤零零地挂着,下面没有任何回复。也许她没看到,也许看到了,
不知如何回复,也许……根本懒得回复。他没有再发任何话,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个头像。
几秒钟后,他退出了对话框,然后,手指悬在「删除好友」的选项上,微微颤抖。最终,
他没有按下去。只是关掉了手机。黑夜吞噬了他年轻却过早染上风霜的身影。
但那双在黑暗中睁开的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,在屈辱和绝望的灰烬深处,悄然改变了。
一种冰冷的、坚硬的东西,正在缓慢凝结。2孤注一掷的起点工地的活儿,李默继续干着。
只是比以往更沉默,更拼命。搬砖,和浆,跑腿,脏活累活抢着干,
仿佛要把所有的力气和情绪都消耗在无休止的体力劳动里。工头老张骂他的次数少了,
偶尔还会拍拍他肩膀,递根劣质烟:「小子,有点血性!这世道,能吃苦是本事!」血性?
李默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他只知道,不能再这样下去。林薇薇的话是毒药,也是淬火剂。
烧掉了他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,也把他骨子里那点不服输的硬气给逼了出来。
休息的时候,别人打牌吹牛,他捡起工地废弃的旧报纸,看上面的新闻,尤其是经济版块。
那些关于股票、关于房地产、关于什么「互联网风口」的陌生词汇,他看得似懂非懂,
却拼命往脑子里记。晚上,他跑到工地附近最便宜的网吧,用省下的饭钱,
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泡在网上,搜索一切能搜到的关于创业、关于赚钱的信息。
论坛里的草根逆袭帖,他翻来覆去地看,分析那些成功者起步时做了什么。
尽管大部分看起来都像天方夜谭。他知道自己起点太低,没学历,没资源,没人脉,
甚至连像样的本钱都没有。但他有的是年轻,有力气,还有被逼到绝境后那股豁出去的狠劲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多月后。工地上一个负责采购小五金和劳保用品的老乡要回老家,
急着把手头一个小供货渠道转出去。东西很杂,螺丝、钳子、手套、安全帽之类的,利润薄,
账期还长,没人愿意接。李默听说了,心里一动。他找到那个老乡,
把自己这几个月攒下的所有钱,加上预支了半个月工钱,凑了两千块,接下了这个渠道,
还有一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手三轮车。从此,李默的生活变成了白天在工地干活,
傍晚蹬着三轮,按照老乡留下的名单,
穿梭于H市各个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和五金店之间送货。风里来雨里去,夏天晒脱皮,
冬天冻裂手。为了省一块钱公交费,
他能蹬着满载的三轮车横穿半个城区;为了追回一笔拖欠的尾款,
他能蹲在别人店门口等到深夜。他老实,送货从不短斤缺两;他嘴笨,但答应的事一定做到。
渐渐地,一些工地的小工头、五金店老板觉得这小伙子实在,愿意跟他长期合作。
他的供货单子慢慢多了起来,三轮车换成了二手小面包车。利润一点点累积,虽然慢,
却踏实。他搬出了工棚,租了一间城中村最便宜的单间,
晚上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可以继续学习。他报名参加了夜校,学基础会计,
学市场营销,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可能对他有用的知识。同时,
他始终关注着城市的发展规划。H市正在向东扩张,新的开发区如火如荼。
靠着积攒的小本钱和夜校学来的粗浅知识,李默开始尝试做更大的建材倒卖。他胆子大,
心细,肯钻研建材质量,价格又比市面略低,在几个新兴工地打开了局面。一次偶然机会,
他听说开发区有个小地块流拍,位置偏,没人看好。李默拿出全部身家,
又想办法借了一部分高息贷款,像个疯狂的赌徒,押上了所有。
那段时间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,每天睁眼就是债务和利息。他吃住在工地临时板房,
亲自监督每一车材料,和工人一起干活,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跑手续。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,
包括当初借他钱的人,都等着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血本无归。然而,
命运第一次向他露出了微笑。半年后,市里一条规划中的主干道调整方案公布,
恰好经过他那块地旁边。地块价值飙升。李默没有贪心,迅速转手,还清债务后,
净赚了他人生第一个五十万。五十万,在当时的H市,足以让一个普通人过上安稳生活。
但李默没有丝毫停歇。他看到了房地产浪潮的威力。他把这五十万作为启动资金,
注册了一个小小的建材公司,不再满足于倒卖,
开始尝试承接一些小型的、别人看不上的分包工程。他比任何人都拼命。亲自跑市场,
拉关系,学技术,控成本。公司最初只有他和两个雇来的老乡。为了省人工,
他自己开车送货,自己下工地检查质量,连续几个月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。他的「默远建材」
靠着低价、保质和不要命般的效率,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硬生生啃下了一块又一块骨头。
三年时间,默远建材从分包小工程,到独立承接小型楼盘的部分建材供应和基础施工。
李默完成了最原始的资本和经验积累。他也愈发清晰地认识到,光靠吃苦和蛮干,
天花板触手可及。他需要更大的舞台,更快的资本运作。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触金融圈子的人,
参加各种创业沙龙、行业交流会。在那里,他穿着廉价的西装,
与那些西装革履、谈吐不凡的精英们格格不入。他能感受到那些隐藏的打量、礼貌的疏离,
甚至是不加掩饰的轻视。他们谈论着天使轮、A轮、IPO,